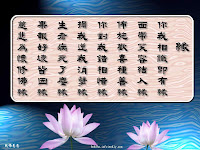侯文詠
2004天夏天遇見的那些水田裡安靜地成長的稻禾、水田裡倒映著無語的天空,慵懶的雲朵,以及滿屋子嘈雜地吃著飯包的人的影像。每次想到這些影像,不知為什麼,莫名其妙地就會稍稍覺得心安了一些。
2002年時我度過了四十歲生日,那年我出版了回顧自已來時路的散文集─「我的天才夢」。到了2003年出版完採訪教育議題的「危險心靈」後,我發現某種心灰意冷的感覺正在蘊釀中。寫完「危險心靈」時,台灣正流行SARS,整個台灣彷彿就要沉淪了。不曉得為什麼,那種末日式的夢魘,竟強烈地呼應著我內在的某種荒蕪。
像我這種在七○年代度過青少年的五年級世代,和台灣的親密關係其實是很特別的。那時候,我們在長大,台灣也在長大。不管是身高、體重,知識、事業,甚至是民主、自由、進步、繁榮……都用一種驚人的面貌,每天在變化。儘管那時候很多事物都還潰乏,可是我們和台灣充滿了希望與生命力,彷彿所有的不義、不公都可以改變,所有的美好都可以實現,所有的努力,都會有所許應……
可是這些事情,到了二十一世紀之後,似乎全部都停滯了。那些我們曾有的想像,理想實現之後,化為愈來愈多的八卦、族群對抗,口水戰,口是心非的教育體系,政治人物,不負責任的政治人物……那種原地踏步的感覺讓每個人都感到無奈。我開始懷疑莫非「變老」就是這種感覺?我不知道是我內在的荒蕪延伸到了我對台灣觀感,或是台灣外在的亂象觸動了我內心的荒蕪。到底是我變老了,台灣變老了,抑或我們就將一起老去?
2004年大選,大選完之後是藍綠抗爭。我在電視螢幕上驚訝地看到了「危險心靈」小說最後的大抗爭,在台灣街頭變成了真實。忽然覺得當我曾經相信的理想變成了這個樣子時,任何的自我安慰、解釋似乎都是多餘。我開始懷疑,如果開始些曾經說服我的許多熱情我都不再相信,我還能寫出什麼來說別人呢?我甚至有種停筆的打算,只覺得說得愈多,無非只是愈增加混亂罷了。
我的心情像是英瑪柏格曼的電影「假面」裡的女主角一樣,一個話劇演員,有一天忽然不想再說話了。我大學時代看第一次看「假面」時無法體會那樣的心情,2003年我讓「危險心靈」裡的小傑最後不再說話。到了2004年,我發現那已經變成了我最真實的心情與渴望了。
●
我大概是在那樣的心情之下,在2004年的夏天展開了一場環島旅行。那似乎是這幾年間唯一沒有出國的一年。我和雅麗開著汽車,用一種不確定會怎麼走,不確定會停在哪裡,不確定走到哪一天結束的方式,展開了那次的環島旅行。
那時雪山隧道還沒打通,我們沿著東北角海岸,一路往東行駛。一路上,除了雅麗之外,我的鏡頭裡面一個人也沒有。我帶著簡單的單眼數位相機,拍了很多照片。那次,我幾乎拍了上千張的天空、雲柔、道路、樹影、海港、船舶、波浪、電線桿……陽光很艷麗。拍出來的照片顏色也很好。奇怪的是,我當時有種很奇怪的心情,透明而清冷,和照片的氛圍很不相同。當時我並沒有去深究,反而是過了很久以後,我才發現在這之前的旅程上,除了雅麗之外,我的鏡頭幾乎沒有拍進任何一個人。那些不說話的天空、不說話的雲朵、不說話的道路、不說話的樹影、不說話的海港、不說話的船舶,不說說的波浪……其實正是我和自已內心的某種深切的對話。
我們的汽車就這樣走走停停。我第一眼注意到那些稻禾是從花蓮往台東的路上。一股巨大的衝動讓我停下汽車,開始拍攝。從此之後的連續好幾天,我被自已被自已的熱情有點嚇了一跳。一路上我幾乎是無法壓抑這樣的衝動。看到了稻禾就想停下來拍照,我拍攝了水田,灌溉的川圳、正在長大的秧苗、遠方的山,靠在山上的雲,雲在水田裡的倒影……我不停地拍照相片,甚至神經質地覺得自已彷彿聽到了那些稻禾正在長大的聲音。我不明白到底是什麼樣的衝動,或者這樣的拍攝到底要帶我走到哪裡去。我像個興緻勃勃的小說讀者,不斷地按下快門的手宛如翻動頁面心情一般,彷彿那一田田不相關的水田之間真的存在著什麼動人的情節似,只要不斷地翻動,就可以看到令人啟發的結局似的。
●
我就這樣一路拍到了池上這個稻米之鄉。街面上到處是讓遊客品嚐池上米的便當餐廳。我走進一家便當店,店裡面有著貼著斗大的海報和文宣,文宣裡一個創始的阿嬤講了一段類似這樣的話(就我記憶所及):
大溪只靠著一樣豆干,用心把豆干作好,就可以養活全鎮的人。因此,不要小看我們賣的只是一個便當,因為除了米之外,我們還多出了滷肉、薑片、醬瓜、青菜……只要用心把每一樣菜都做好,我們就有比別人更多的機會……
那是一個從台灣光復之後,一直賣到了現在的便當。我和雅麗買了兩個便當,和許多不認識的遊客一起坐在一吃飯。大人、小孩,嘈雜的聲音、零亂的感覺,一切的一切,都是在台灣每天活著的日常生活裡,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聲音。我不知道是因為我的心情,或許是因為在螢幕上看到的失去了很多很多的台灣,或許是我一路上拍了那麼多的稻禾的緣故……在那樣的普通裡,卻有了一種很不普通的氛圍。那種氛圍,讓我感受到米飯的香味─那種每天吃著的米飯,一直都有的香味。
吃完飯,我拿起相機,隨手拍下了幾張照片。我甚至沒有選取任何角度,考慮光線,也沒有故意避開桌面上的那些狼藉,就按下了快門。在那些從許多標準來看都不符合美學原則的照片裡,它仍然保留下來了某種看不見,我卻很在乎的感覺。那是一種說不出來的感覺,那種感覺讓我不管發生了什麼,只要還有那麼多人繼續用這種最簡單的專注耕作著,勞動著,吃著。只要那種專注還在,那麼,看起來亂糟糟的一切,就不可能讓我們真正失去什麼。
●
2004年的夏天的環島旅行其實還走了許多路。那幾張吃飯的照片為我瘋狂的稻田攝影畫下了一個句號─或者應該說開啟了新的句子。我注意到在那幾張攝影之後,我的相片裡又開始出現了人。有種了一輩子米,終於種出「冠軍米」的老農,有從台北返鄉,虧損了多年,但無論如何也要幫助村落的農夫,在WTO之後走出一條自已的路,栽培出高品質的有機米的碾米商人。有從城市回歸故鄉,決定開創屬於自己理想風格民宿的年輕人。有窮鄉僻壤賣著水果、烤肉的母親,不停地告訴我他的兒子是數學資優,雖然經濟的負擔很大,可是無論如何她一定要支持他代表台灣去美國參加比賽……
到現在為止(2007年秋天),我仍然還沒有弄清楚2004年夏天的那次旅行到底對我產生了什麼影響。2005年之後,我開始投入「危險心靈」的連續劇拍攝,同時也支援「白色巨塔」所有醫療相關的醫療拍攝。2006年,我又一頭鑽進書桌裡,寫了長篇小說:「靈魂擁抱」。這些工作對我而言並不輕鬆。每次搞得灰頭土臉時,我總不免要問自己,為什麼明明還有許多別的看起來顯是更容易選擇時,我卻總是選擇了這些最吃力不討好,最沒有人願意做的事來做?
就如同我對於自已,對於台灣的許多思考與問題一直沒有很好答案一樣,這些問題向來也是如此。不過這幾年間,每當被自已的選擇的事情搞到聲嘶力竭、頭破血流,甚至是心灰意冷時,我的心裡常常就會浮起2004天夏天遇見的那些水田裡安靜地成長的稻禾、水田裡倒映著無語的天空,慵懶的雲朵,以及滿屋子嘈雜地吃著飯包的人的影像。
每次想到這些影像,不知為什麼,莫名其妙地就稍稍覺得心安了一些。
>>>>2007/12/1 中國時報 人間副刊
來源:電子郵件
skip to main |
skip to sidebar
"抖落一身塵霜,邀得滿心陽光" - Leave Dirt There, Be Self Fair.
一絮心香,滿懷陽光,墨客文章,滌塵融霜